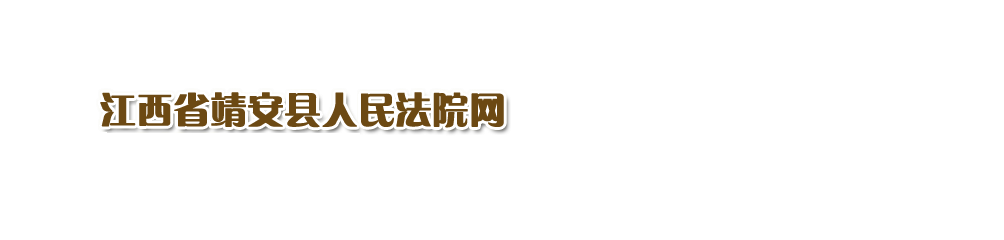贾小义自1994年调入法院以来,从书记员到庭长,从曾经懵懂的法院工作门外汉,到如今的全市“调解能手”,全省“优秀法官”。十几年来,始终工作在审判工作第一线,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一名人民法官的追求。
有百分之一调解的可能,就要付出百分之百的辛苦努力
也许,对于法官来说,对案件作出公正的判决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因为,这原本就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但重要的是能够做到每一件案件都能圆满地解决,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李某和杨某曾是邻居,打小就一起长大,是相识数十年的好友。李某在县直机关任职,杨某在村里工作,多年来二人交往甚密。2009年7月2日,李某回家探亲后回城,杨某主动驾车相送。中午时分,当杨某驾车行至县城云头山路段时,因头天晚上二人交谈甚欢,直到深夜仍未入眠,疲劳过度,汽车不慎撞到公路边的树上,两人均受重伤。杨自己花费了四五万元医药费,李某尽管在多家医院接受治疗,终因伤势特别严重,腰部以下仍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左眼失明、被鉴定为一级伤残,需终身护理。李某在耗费了30余万元后,难以为继,后续治疗陷入停顿。
面对巨额的医疗费用和后续护理所带来的经济上和精神上的负担,李某家属与杨某家属多次协商均不欢而散。后李某家属以李某名义向法院起诉,要求杨某赔偿九十余万元。面对诉讼,杨某心情沉重,家里可算到财产就是一幢旧土屋和1500元左右的月工资,根本无法承受巨额赔偿。在情理上,杨某的行为确是“好意同乘”,值得倡导,可是司法界主流观点认为驾驶者有过错仍应当赔偿。
受案后,他没有按惯例安排开庭审理,决定先从双方几十年的感情入手,寻找调解纠纷的机会。此时李某仍在南昌住院,他专程去到南昌,在李某的病床前与他交谈了近二小时。了解到其实李某没有向杨某索赔的意愿,只是自己瘫痪,生活无法自理,需要家人照料,要服从家里人的意见。
杨某家人对李某的诉讼表示不能接受。回靖安后,他首先与杨某沟通,杨某表示致使李某受伤非常内疚,自己愿意赔偿,但自己的经济能力确实有限,无力承担。
与杨某、李某交谈后,我看到了调解的希望,提议陪杨某到南昌看望李某。杨某有些顾虑,决定先由代理人去探明李的病情和真意。从南昌回来后,他转达了李某想与杨某面谈的意向,之后又陪同杨某第三次到南昌与李某面对面的商谈。李某回靖安治疗后,他努力说服杨某再次去探望李某。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数轮交谈协商,杨某、李某家庭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最终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多年的友谊在这份调解协议中也得以延续。
看到原本对立的原被告双方最终握手言和,这是作为一名法官的最大快乐。几年来,他每年审理和参与审理的案件都在100余件,承办的民事案件调解和撤诉率年均达70%,无一反悔或申诉。
“深入群众”省了法官的力,“能动司法”得了百姓的心
“能动司法”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要求法官真正深入群众,到“老百姓家门口调解案件”,就地缓解矛盾纠纷,只有这样,才能受到老百姓的真心欢迎。
2008年4月初,靖安县开发建设新工业园区,香田乡黄龙村瓦桥组部分土地被征收,在商定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时,胡某一家十余人与村民小组意见发生激烈冲突。
原来,胡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才落户该村的,多数人主张只能按其他村民的60%补偿标准参与分配。胡家坚决不同意。胡讲宪法赋予公民平等的权利,作为瓦桥的村民应享有与其他村民同等的受偿权。因为补偿款分配方案不能确定,调整土地的方案也无法确定。
时值春耕季节,有地没法耕种,农民心急如焚。十几位农民到乡政府反映情况,要求尽快确定方案,有的甚至到县政府上访。为尽快解决纠纷,防止事态扩大,他受命前往瓦桥着手调处纠纷。
他先后在田间地头找了十多位村民谈心,每晚都到农户家聊家常。经过广泛了解才得知:村民经历过土地改革,农具、耕牛及其它生产工具都交给了村民小组,正因为有他们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繁衍,这片土地才得以延续至今。依情,村民在理;依法,胡有法可依。作为一名法官,既要维护法律的权威,也要兼顾利益平衡。
经过他挨家挨户的不懈努力协商沟通,我提出了调解方案:胡家享受与其他村民同等的权益,但胡家应从补偿款中提留一定比例作为村民小组举办公益事业的经费,由村民小组集体支配。该方案得到包括胡家在内的全体村民一致同意,全村29户代表均在方案上签字。据了解,后来该方案为其它乡、镇的村民小组分配同类补偿款所效仿。
法官只有主动下沉,深入群众,变“受理立案”为“诉前调解”, 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庭前诉外,消化在基层和萌芽状态,从群众中吸取灵感、智慧和力量,才能脚踏实地,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最终赢得人民群众的赞许认可。
以平常之心对待恶意威胁,以仁爱之心善待当事人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面对群众,坚持笑脸相迎,平等对待;面对威胁,不偏不倚,保持中立;始终坚持相信组织,相信群众,善待他人,善待自己,对利诱威胁都坦然面对。
他审理过这样一起继承纠纷案件:有一老妇共有子女6人,在老妇人去世后,处理父、母遗产时,兄弟们协商将父母生前的一套房改房作价转让给老四,老四按协商确定的价款分别支付给了其它兄弟,众兄弟都得到了自己应得的一份。几年过后,因城市扩张,房子要拆迁,随着房价上涨,按估算老四可以获得较多的补偿款。此时,老二很不乐意,纠集其它兄弟向老四要求分补偿款并起诉到法院。并直说房产登记在父亲名下没有过户,房屋还是父亲的。
依法,兄弟协商确定处分了父母的遗产且履行完毕,房屋应归老四所有;依理,房屋转给了老四,老四当年出了钱给其他兄弟,房屋也应归老四。他反复向老二解释,老二听不进,又是托人说情,暗示如判决对其有利,则可以对我有所“表示”;同时又威胁说,一旦作出不利判决将不断上访,甚至会做出对他有不利的“举动”。但在确凿的事实面前,他还是顶住了各方说情的压力,拒绝了金钱的诱惑,依法驳回了他们的诉讼请求,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公生明,廉生威。处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金钱的诱惑、人情的压力,对每一位法官来说无疑是一种严峻的考验,要做一名好法官,坚持公正办案,就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干干净净做人,认认真真办案,绝不能玷污法律的神圣。
为多占土地亲戚撕破了脸,真情调解挽回了亲情
对大多数民事审判,法官一定不要怕受气,只有耐着性子,悉心倾听,才能拉近当事人与法官的感情距离,也才能得到当事人的最大支持理解。
2007年3月,水口乡三峡移民刘某与邻居丁某因土地侵占而发生了纠纷,最后双方对簿公堂。
刘某和丁某都是从重庆云阳移居靖安县的移民,两家的房屋仅一墙相隔,水田和旱田互为上下或左右相邻。丁某长期在外务工,春播时节才返乡播种。2007年3月份,丁某春耕时,发现田埂有向他水田一侧偏移的现象,便找到刘某商议,要求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双方意见不同,引起争吵,刘某与丁某的老婆还发生了肢体冲突。
后来,双方矛盾逐渐升级,丁某将田埂推翻,重往刘某的水田一侧重修了一田埂。刘某带着女儿、女婿到丁某家吵闹。丁某拖了一车杂木,堵住了刘某家的通道,一直过去了半个月。尽管经过乡、村干部以及派出所多次调解,双方依旧没有矛盾缓和的迹象,后来发展到两家的鸡、鸭走到对方的家里或场地都会追着打。刘某感到无法生活下去,向相关部门要求回迁。无奈之下,经过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引导,刘某走进了法院。
针对刘某起诉,丁某感到备加委屈,说到自己不仅水田被占,还挨了打。
在调查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对丁、刘家吵架、打架,移民新村竞无人劝解也无人打探,我就想到这积怨背后,可能另有隐情。
经走访当地的移民了解到,其实丁家和刘家具有亲戚关系,移居靖安前两家就有矛盾,到靖安后因丁家建房覆盖了刘家的下水道,有过争吵;丁家认为刘家多占了丁某的旱地也发生过争吵,但都没有解决。另外还有其它琐事引发的纠纷等。
在开庭之前,他有时中午来到刘家拉拉家常,有时下乡办案路过时到丁家坐坐谈谈。有时候联系他们到办公室聊聊,经过一段时间沟通、交流及调查。弄清了事实,把握了双方的心理状态,在村委会的配合下,决定在当地开庭。
开庭那天,刘某、丁某及双方家人都准时到庭。旁边还坐着几位长老,他们是村里的原住民,对双方田地界址十分清楚。他特意邀请他们旁听及鉴别哪一方讲事实、讲道理。
“哑巴吃汤圆,心里有数”。见到到场的一群人,刘某和丁某都表示要与我单独交谈,刘某承认挖地时无意挖过界,占用了丁某的一点旱地,愿意退回。丁某则表示立即将田埂恢复原址。
一场看似复杂的纠纷就这样被我化解了,两家之间的关系也得到极大缓和。
詹红荔曾说过:“一个共产党员,不论分内分外,如果需要,都义无反顾;一个人民法官,不论庭内庭外,如果需要,都责无旁贷”。在法院工作的十几年间,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更没有催人泪下的事迹,接触的也多是东家长、西家短的婆妈“小事”,但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要努力做好,尽一切可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只有在平凡中坚持,恪尽职守,忠诚为民,才能对得起人民的期待和自己的良心,才能在坚持中铸就属于自己的辉煌。
今天是: